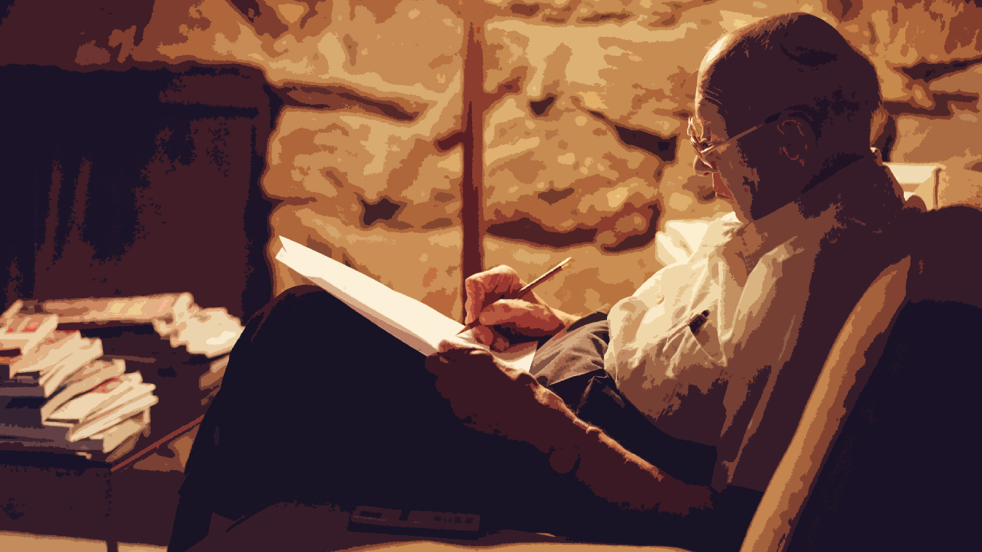在生活裡發現自己─ 述小說家彼得.杜拉克
一、寫小說的杜拉克
彼得.杜拉克寫過三本敘事作品:《旁觀者》(Adventures of a Bystander,1978)、《最後的美好世界》(The Last of All Possible Worlds,1982)、《行善的誘惑》(The Temptation to Do Good,1984)。《旁觀者》是杜拉克的個人生活史,也是他的精神自傳。《最後的美好世界》和《行善的誘惑》則是純正的虛構文學。杜拉克所有作品中,這兩本小說或許是最少被關注與被討論的。作為小說,它們理應是最易讀的作品。作為管理學大師的小說,它們卻可能是最難讀的作品。大師為何要在晚年寫小說?他打算藉助小說說些什麼?這是一個問題,很要緊的問題。
晚年的回顧文章裡,杜拉克建議讀者把自己視為「社會生態學家」(〈 一個社會生態學家的省思〉,1992)。社會生態學家的使命之一,是觀察世界的變遷、解釋變遷的成因、預判變遷的後果。社會生態學家的使命之二,是在動蕩的世界裡守住文明的基本價值,並從這些基本價值中引申出未來社會的新願景。觀察世界、描述其變化,並對變化做出解釋,這通常被視為歷史學家的工作。捍衛文明的基本價值,這通常被視為道德哲學、政治哲學乃至神學的職責。為未來社會勾勒藍圖、提供願景,這似乎是20 世紀方興未艾的「未來學」的專利。杜拉克從不以歷史學家、政治哲學家、道德哲學家、神學家、未來學家自居。但他的寫作,往往同時包含上述所有面相。他的假想讀者不是大學課堂或書齋裡的專家,而是那些渴望在世界上有所行動的人。這些渴望行動的人,不只需要具體的行動指南,還需要在更廣闊的視野裡理解自己的行動,領會行動的使命與願景。作為社會生態學家,他肩負的第三項使命,是捍衛語言、教育大眾。捍衛語言,是用明晰的語言捍衛文明的基本價值、基本信念。教育大眾,是讓語言重新成為人們思考、論辯、溝通的工具。唯有學會用語言思考、溝通的人們,才有能力抵禦那些禁止人們思考、溝通的語言。
捍衛語言、教育大眾,正是杜拉克為自己確定的寫作使命。他說,「社會生態學家不必是偉大的作家,但他們必須是受到尊重的作家,是關心社會的作家。」在他心目中,有一份符合這項標準的作家清單,包括歷史學者、政治學家、社會學家、經濟學家,也包括記者、小說家。他們的共同之處是,能用明晰的語言,講出引發普通讀者關切的故事。這樣的作家,在20 世紀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他們屬於一個悠久卻不幸瀕臨斷絕的寫作傳統。法語裡有一個詞形容這類作家:moralistes。倘若翻譯成漢語,或許可以稱之為「載道派」。20 世紀之前,「載道派」的寫作本就不限文體與學科。哲學家會把哲學講成故事,小說家會在小說裡討論道德和上帝。作者們操心的只是用切當的方式談論恰當的話題,而不會太過在意自己的專業身份。寫小說、散文、詩,還是論文,不是寫作者的本質區別。文以載道,還是文以自耀,才是寫作者的本質區別。杜拉克夫人曾說:「彼得熱愛寫作,一生都在寫,但他從來沒有為了使自己顯得重要而寫作。」(邵明路先生轉述)。
僅僅把杜拉克視為「管理學大師」的讀者,恐怕不會對大師的小說感興趣。就算大師的「管理學」作品,他們可能也只有局部興趣。但若回歸「文以載道」的傳統,讀者或許可以從中讀到一個更完整的杜拉克。剖析公司治理結構的杜拉克、為知識工作者提供建議的杜拉克、預判未來經濟趨勢的杜拉克、追憶老祖母的杜拉克、寫小說的杜拉克,其實是在傳達同樣的消息。這個消息,就是他所珍視的自由、平等、人的尊嚴。這是文明的基本價值和信念,是文明最為寶貴的部分,也是最為脆弱的部分。一部人類歷史,是一次又一次發現它們的故事,也是一次又一次毀掉它們的故事,更是一次又一次重建它們的故事。同一個故事,可以有不同的講法。管理學大師杜拉克,把這個故事的綱要寫進《公司的概念》(Concept of the Corporation,1946)這樣的管理學論文。可是,故事的精微之味,總在綱要之外。晚年的杜拉克,把它們寫進兩部小說。
二、責任的發現
杜拉克一生寫作的起點和樞紐,是對極權主義的識別和剖析。而極權主義的產生,根源於「經濟人社會」的內在邏輯(《 經濟人的終結》The End of Economic Man,1939)。19 世紀的歐洲,是資本主義的盛世,盛世之中,也潛藏著危機。所謂「資本主義」,不只是一套經濟運轉的制度,還承載著一整套信念。自由、平等、民主、人的尊嚴,這些歐洲文明的基本信念可以追溯到古希臘,更在基督教教義裡獲得了明確表達。資本主義並未創造它們,只是從此前的世代繼承了它們。這些價值和信念,並非抽象的說辭,而是具體的生活。不同的世代,人們把對自由、平等、尊嚴的渴望投射到不同的生活場域。13、14 世紀的人們,在信仰世界尋求自由、平等、尊嚴。杜拉克稱之為「靈性人」的世代。17 世紀的人們,在思想領域尋求自由、平等、尊嚴。杜拉克稱之為「智性人」的世代。「智性人」之後,是「政治人」的世代,人們試圖在政治生活中實現自由、平等、尊嚴。而19 世紀,日益成為「經濟人」的世紀。「經濟人」的意思是說,人們把所有對自由、平等、尊嚴的渴望投射到經濟生活中。整個社會的普遍期待是:隨著經濟的發展、繁盛,自由、平等、尊嚴就會自動實現。這是資本主義的基本承諾。然而,資本主義無法實現這個承諾。19 世紀的資本主義,帶來了繁榮,也帶來了前所未有的階級撕裂、階級鬥爭。這當然與人們對自由、平等、尊嚴的期盼背道而馳。馬克思主義準確地揭示了資本主義的自相矛盾,並且承諾用一套截然相反的經濟運作方式,幫人們實現資本主義的未竟承諾。事實是,馬克思主義的經濟模式非但無法消弭經濟上的不平等,反而可能製造更深刻的不平等。控訴階級鬥爭的馬克思主義,不是消滅了階級鬥爭,而是把社會拖入某種更殘酷的鬥爭之中。杜拉克說,資本主義、馬克思主義看似對立,實則是「經濟人」世代的雙生子。它們的共享邏輯是:只要找到正確的經濟模式,自由、平等、尊嚴就會自動實現。於是,人們對自由、平等的渴望,就變質成對某種經濟模式、制度公式的依賴、崇拜,不是無限相信這一種,就是無限相信那一種。20 世紀前30 年的教訓是:人們發現兩種希望都破滅了。無論哪種經濟模式,都不能實現它們預先承諾的自由、平等、尊嚴。希望破滅的人群,陷入絕望。絕望的人,不是什麼都不信,而是願意相信任何非理性的神話,或曰謊言。至於製造謊言的瘋子,絕望的群眾視之為神。為了效忠於神,群眾願意踐踏曾經珍視的一切。這就是極權主義的社會心理根源。要想抵禦極權,唯一的希望,就是建設某種「非經濟人」的新社會。那樣的新社會,必須有豐富的生活場域,人們得以在其中安頓自由、平等、尊嚴的渴望。那樣的新社會,不是不注重經濟,而是讓經濟發展重新找到合理的目的。《公司的概念》、《新社會》(The New Society,1949)之後,管理學家杜拉克主要致力於新社會的構想和實踐。
如果說極權主義是杜拉克終身思考的樞紐,那麼《最後的美好世界》和《行善的誘惑》描述的恰好是極權之前、極權之後,一舊一新兩個世界。
《最後的美好世界》的主要情節,發生於1906 年。這個時間點,既可以看成歐洲資本主義盛世的黃昏,也可以看成不久之後文明浩劫的序幕。小說的主要人物,來自歐洲的四個金融家族。最年長的亞瑟.萊夫尼茲男爵(第四部)生於1816 年,他在故事發生的時候已經去世。小說第一部的主角索別斯基親王生於1840 年,第二部的主角辛頓生於1843 年,第三部的主角莫森索爾生於1850 年。時間來到1906 年,三位主人公都已年屆耳順,都已功成名就,也都正面臨著各自的生活危機。而他們的危機,既關乎19 世紀歐洲的資本主義發展史,也關乎每個人的私人生命史。小說家杜拉克的雄心,是把這兩部歷史聯結起來。
小說裡的幾個家族,都隨著歐洲資本主義勃興而崛起。亞瑟.萊夫尼茲男爵的岳父,抓住了中歐城市的第一波擴張浪潮,投身城市建築和鐵路。在當時的人看來,這是一場豪賭。到了亞瑟和他的內兄這一代,鐵路和城市建設不但使他們獲得巨大的財富,也深刻改變了歐洲的景觀風貌。索別斯基親王、辛頓、莫森索爾他們,要算是大潮裡的第三代弄潮者了。他們趕上了銀行業的蓬勃發展。他們這一代人裡,最偉大的銀行家,要數西門子和摩根。德國人西門子創辦德意志銀行,願景是讓當時仍處農業社會的德國工業化。美國人摩根的願景,則是通過銀行業助力一個工業化的美洲大陸。辛頓和莫森索爾,也屬於西門子、摩根式的銀行家。他們終生與資本打交道,但並不以操弄資本為目標。他們明確知道資本事業的使命:促成歐洲民族國家的工業化。正是在這種明確的使命意識之下,辛頓和莫森索爾聯合創辦了倫敦奧地利銀行。辛頓是董事長,莫森索爾是總裁,索別斯基親王是大股東和名譽董事長。短短20 年時間,倫敦奧地利銀行成為歐洲最成功的銀行之一。也正是在19 世紀最後的20 多年裡,歐洲主要民族國家完成了工業化進程。到了1906 年,辛頓和莫森索爾雙雙意識到,世界湧動著新潮流,銀行家也必須重新理解自己的使命。辛頓發現,歐洲的工業化已經完成,接下來的大趨勢是世界的工業化。銀行業必須對此做好準備,也必須為此做出貢獻。莫森索爾發現,歐洲政治、經濟格局真正決定性的變化,是中產階級的興起。這股浪潮將使國與國之間的經濟界限日趨模糊,也將讓社會主義者時常掛在嘴邊的「階級」分野成為空談。說英語的人、說德語的人、說捷克語的人、銀行高管、產業工人,將會愈來愈彼此依存,而非彼此對立。銀行,必須擴大所有權基礎,不可以滿足於充當少數富豪的致富工具。於是,在1906 年,倫敦奧地利銀行面臨著改組和轉型。轉型,不是因為它的失敗,而是因為它的成功。辛頓和莫森索爾都意識到,過去的成功可能成為未來的枷鎖。小說的第三部,莫森索爾準備擔起責任,主導這次轉型。
與此同時,通過銀行聯繫起來的三個人,也都面臨著各自生活的轉折點。
索別斯基親王正打算辭去擔任了二十多年奧匈帝國駐詹姆斯宮大使。他曾經是歐洲最成功的外交官。他的外交生涯發跡於1871 年的巴黎公社時期。當時留守巴黎的他,通過奧地利大使館收留了幾百名不幸的德裔平民。他也目睹了巴黎城中肆無忌憚的仇恨和暴力。暴徒差一點就對他動了私刑。當然,他也目睹了鎮壓暴徒的政府軍,同樣的野蠻殘暴,同樣的燒殺搶奪。那個時代,人們習慣於把巴黎公社事件視為「階級鬥爭」。在馬克思敘述裡,這是革命英雄對剝削者反抗的故事,這是一個捨命追求美好新世界的故事。可是,親歷其事的索別斯基知道,主宰群眾的,不是什麼階級情誼、革命理想,而是憤怒、仇恨、嫉妒,以及殺人的慾望。三十多年以後,索別斯基發現,整個歐洲有可能陷入一場更大的浩劫。奧匈帝國高層湧動著亢奮的戰爭情緒。不只奧地利,不負責任的政客、莽撞的青年軍官遍佈歐洲各地,他們都在期盼著戰爭,甚至盼著從戰爭中獲利。身為外交官,索別斯基有責任傳達國家意志。身為有經驗和良知的歐洲人,索別斯基明確反對戰爭。他反對戰爭,不是因為戰爭勝負難料,而是因為戰爭必將毀掉文明。在道義良知和職業責任的衝突之間,他決定辭職。
索別斯基辭職,還因為另外幾重責任。1871 年,在救助了數百平民的同時,他也搭救了後來的妻子。他對妻子的感情,與其說是愛,不如說是一份如兄如父的責任。故事發生的時候,他的妻子正陷入一場忘年的婚外戀之中。他早就察覺這場戀情,甚至默許這場戀情。但是這場戀情很難有個體面的收場,而受傷的那一方,必定是他的妻子。他不想讓妻子受傷,也不想讓另一位當事人難堪。化解危機的最佳選擇,就是離開倫敦。除去對妻子的責任,索別斯基還決心擔起對私生女的責任。亨利耶塔是他的私生女,也是他在世上唯一愛著的人。他愛她,不是因為她的美德。相反地,他對她的功利、市儈、貪婪了如指掌。儘管如此,他還是愛她。因為這份愛的承諾,是在亨利耶塔出生之時就許下的。更重要的是,這項承諾是他對自己,而不是對亨利耶塔許下的。亨利耶塔預見到戰爭將要爆發,想幫平庸的丈夫藉著戰爭的機會撈上一把。為此,她求索別斯基利用身分走走門路。索別斯基做了亨利耶塔求他做的事。
身為政治家,他反對戰爭,更厭惡那些想從戰爭中撈到好處的人。而身為父親,他幫女婿從將要爆發的戰爭裡撈了好處。身為紳士,他的座右銘是,不做讓自己變得面目可憎之事。他辭職,因為他不想做這樣的事─成為戰爭販子的幫兇;他辭職,卻又因為他做了這樣的事─利用職權,助人投機,並且是投戰爭之機。辭職這個行為,既是他對自己信念的堅持,似乎也是他對自己過失的懲罰。
從外部視角看來,索別斯基有高貴的出身,有巨大的財富,有顯赫的聲望。可是,杜拉克要寫的,並非他的成功,而是他在人生關鍵時刻的無奈。面對即將吞沒歐洲的戰爭狂熱,他無奈。面對妻子的情慾風波,他無奈。面對女兒的予取予求,他無奈。所有這些無奈,從生活中漸次湧現,最終匯聚一處,構成了索別斯基的問題情境。索別斯基不止一次想要逃避,最終還是選擇面對、決斷。他的決斷並不完美,甚至包含有意為之的職業過失。他的決斷也不能改變什麼,既不可能阻止戰爭,也不大可能讓妻子多些快樂、女兒少些貪婪。但他的決斷至少是一種堅持。這個在無奈中犯下過失的人,發現自己必須盡力守住一些必須守住的價值。否則,他就沒辦法跟自己相處。
杜拉克筆下的辛頓和莫森索爾,也面臨著跟索別斯基相似的境遇。他們既要面對事業上的重大抉擇,又要面對私人生活史上的重要轉折。作為銀行家,他們得一次又一次重新定義願景和使命。作為丈夫、情人、父親,他們也不斷發現責任、承擔責任。對他們而言,公共事務、私人生活並不是割裂的。他們各自痛苦著、掙扎著、悔恨著、逃避著、補救著,決斷著。他們終於意識到,無論身為大使、總裁,還是丈夫、情人、父親,所有的身份、機緣都匯聚成一個完整的故事:人對責任的發現和承擔。
《最後的美好世界》寫的正是人對責任的發現和承擔的故事。杜拉克筆下的資本家們,在世界政經大潮中發現責任,也在婚姻生活、情慾生活中發現責任。在杜拉克的歷史景觀裡,19 世紀是「經濟人」的世代。可是,19 世紀畢竟頗有成就。甚至,在經歷過兩次浩劫的20 世紀居民看來,19 世紀是值得懷念的「昨日世界」(茨威格語)。之所以如此,正是因為這個「經濟人」的世代還有能力造就眾多尚未塌陷成「經濟人」的精英人物。索別斯基、辛頓、莫森索爾就是這樣的人物。杜拉克沒有把這些資本家寫成馬克思主義史學、文學裡的「剝削者」、「大反派」,也沒有把他們寫成世俗完人或聖徒。他們各有各的荒唐,各有各的懦弱、虛榮,乃至冷酷。但他們都是能在生活亂流裡識別責任、擔荷責任的人。對他們而言,責任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在具體生活中湧現出來的具體挑戰。他們願意直面挑戰,為了應對挑戰,他們有勇氣在關鍵時刻做出取捨。他們的動力只有一個:每天早上攬鏡自照,不能成為自己討厭的人。小說裡,杜拉克借索別斯基之口說出了這條生活原則:
然而,我還是不想早上攬鏡自照時看到一張皮條客的臉。我稱為紳士的人都不想這樣。
這條原則看似淺顯,實則頗具深意。一個時常攬鏡自照、自我審視的人,是一個有能力與自己進行道德對話的人。杜拉克所謂的「經濟人」,恰恰喪失了此種能力。喪失了與自己進行道德對話的能力,也就喪失了對責任的理解力。對這樣的「經濟人」而言,「責任」毫無價值,除非可以換算成資本,或是生產力。
三、辦公室裡的神性與魔性
《行善的誘惑》的主要情節,發生於1979 年到1980 年的數月之間,地點從歐洲移至美國。世界大戰結束多年,世界逐漸從戰火中復甦。美國更是代表著浴火重生的自由世界的方向和希望。以這個充滿樂觀情緒的時代和地方為背景,杜拉克寫下一個頗為陰鬱的故事。
海因茲.齊瑪曼神父是聖葉理諾大學的校長。聖葉理諾是一所天主教大學。25 年前,這所大學只是當地天主教區的一個教育服務機構。其職責,是為天主教家庭的孩子提供就學機會。僅僅用了25 年,海因茲神父讓它變成一所有天主教背景的現代大學。它不再只是滿足於為教區子女提供就學機會,它已經有能力與第一流的世俗大學在學術上一較高下。化學系打算解聘一位教師,名叫霍洛威的教授實在不能勝任自己的職位。霍洛威太太拉著丈夫闖進校長辦公室,要求校長主持公道。海因茲神父知道,化學系的決定毫無問題。讓他憤怒的只有一件事:這個名叫霍洛威的男人怎麼可以活得如此怯懦猥瑣,人怎麼可以把自己的生活糟蹋成這個樣子。他想起自己不只是校長,還是神父,至少是一名基督徒。他的信仰和教養告訴他,作為基督徒,他有責任減輕一個可憐靈魂的痛苦,把他從自我糟踐、自我憎恨的泥沼中救出來。於是,他給女子學院打了電話,推薦霍洛威去那裡承擔高中水平的課程。作為校長,他不該打這個電話。作為基督徒,他打了這個電話。這只是一天早上發生的不太愉快的小事,就像做工精良的鞋裡進了一粒沙子。很快,一粒沙子引發了一場雪崩。簡單地說,大學癱瘓了。學校的理念、管理的機制、校長的信譽和領導力,都遇到了危機。校長仍然掌握大權,卻喪失了權威。就連校長本人,也喪失了對自己的信任。校務照舊運轉。但人人都知道災難即將降臨,人人都束手等著那一刻,也有人盼著從那一刻賺些好處。
《最後的美好世界》是一個關於「發現」的故事。《行善的誘惑》同樣是一個關於「發現」的故事。聖葉理諾大學的人們,正在經歷一場看似波瀾不驚其實性命攸關的危機。唯有身處這樣重大的危機中,人才可能觸碰某種更重要卻也更隱祕的生活維度。比如,海因茲神父和他的朋友們,就是在這場危機的敦促之下,重新思考塵世生活的中的神性與魔性。
海因茲神父一度堅信,自己奮發工作,唯一的目的是「為上帝增光」。這個信念一直是他的力量源泉。可是,霍洛威夫婦的鬧劇之後,他猛然意識到,自己的動機並非那麼單純。「一切不過是虛榮心、個人野心、權勢、私心而已,一切只不過是想證明自己是個偉大人物而已」。一下子,他「體內的全部鬥志似乎都被抽空了」,他不知道「為何工作」,「為誰工作」了。他的朋友,精神醫生貝柯維奇說:「可憐的海因茲,他再也無法回去30 年來保護著他的那個避風港了。從此他必須像我們其他人那樣,辛苦學習如何懷著羞愧與罪惡感、自我懷疑與混沌無明,生存下去。」
「自我懷疑與混沌無明的狀態下生活」,這恰恰是人的本真狀態。純然的聖徒、純然的禽獸,都是人對自身的誤解。以為自己或某人可以成為純然的聖徒,正是這種誤解,使人樂於實施獨裁,樂於接受獨裁。以為自己不過像禽獸那樣是慾望的囚徒,正是這種誤解,讓人心甘情願淪為烏合之眾。前一種誤解,讓人把自己當成上帝;後一種誤解,讓人根本否認上帝。正是這兩種誤解的合謀,讓惡魔有機可乘。
從亢奮自信到自我懷疑以致自我否定,這是一種寶貴的自我發現。海因茲神父終於從自己卓有成效的工作中辨別出驕傲、虛榮。這種自我否定,其實是對人神關係的校正。從此,他無法再把對自己的崇拜和對上帝的奉獻混淆起來。可是,自我發現不該到此結束。海因茲神父的朋友不斷提醒他注意事情的另一面:一個自以為全心全意「為上帝增光」的人,遲早會在自己身上發現不潔;但這並不妨礙一個人帶著不潔做出「為上帝增光」的工作。傲慢、虛榮、自私是人性的胎記,為上帝增光的渴望,同樣深植人性之中。發現前者,才能治癒自我崇拜時的亢奮;發現後者,才能治癒自我否定後的癱瘓。前一個發現,讓人從亢奮自信變得憂心忡忡;後一個發現,讓人帶著憂心忡忡勇猛精進。
海因茲神父和他的朋友發現,還有一種東西,也深植於人性之中,那就是魔性。精神醫生貝柯維奇是猶太人,青年時代鑽研神學,立志成為拉比。後來,人間種種荒唐暴行讓他對上帝失望。他告訴自己,既然上帝不存在,那麼靈魂也不存在。既然拯救靈魂是一件虛妄之事,那麼唯一值得做的,就是醫治心靈。於是,他成為一名心理醫生。他旁觀了聖葉理諾校園鬧劇的全部過程。一度,他認為問題的本質是個人的、群體的精神疾病。但是最後,他終於意識到,這個故事裡不只有病人,還有罪人:「經歷了聖葉理諾大學發生的種種後,我知道邪惡勢力的確存在。」這位一度把世間亂象歸咎於「病」的醫生,重新發現了「魔性」和「罪惡」。於是,他決定走進教堂,接受神父的指引:「我不知道能不能重新找回信仰,但現在我知道我需要它。」
這同樣是一樁重大發現。它表明,後極權世界其實離極權僅有一步之遙。所謂「魔性」,不只是大姦巨惡之徒的專利,那些庸常之輩身上展現的「魔性」往往更加令人毛骨悚然。小說裡,杜拉克寫了兩位成果斐然的教授。他們都對海因茲神父抱有好感,但都在校園風波裡一言不發。理由是,他們擔心因為一句誠實的話斷送舒適生活和錦繡前程。《旁觀者》裡,杜拉克寫過一位成就卓越的化學家和自由主義者。納粹佔領了大學,並向全體教師訓話。一派汙言穢語之後,化學家站起身來、清清喉嚨,只問了一個問題:「生理學的研究經費是否可以增加?」(〈 怪獸與綿羊〉)30 年代的奧地利教授、70 年代的美國教授身上,顯現著同一種「魔性」。這種「魔性」,曾經在20 世紀30 年代肆虐世界,也可能在後集權世界的任何地方重新醒來。《行善的誘惑》這齣辦公室風波,是杜拉克寫給後極權世界的極權預警、極權寓言。
《最後的美好世界》講的是人對責任的發現。《行善的誘惑》講的是人可能在危機之中忽然喪失對責任的理解。此時,他不得不面對更深刻更隱祕的生活維度:現實世界裡的神性和魔性。大多時候,這個隱祕的維度被日常事務的一地雞毛掩蓋了。
20 世紀偉大作家中,杜拉克或許是極少數專注於為辦公室裡的知識工作者寫作的人。20 世紀的偉大作家中,杜拉克或許也是極少數認真談論現代世界的神性、魔性的人。他堅信他的讀者需要這樣的知識,只是他們自己未必知道。
四、教材之外的管理學
《最後的美好世界》和《行善的誘惑》的確是一位管理學大師的小說。因為,兩本小說都用大量筆墨敘寫杜拉克在管理學教材中關心的話題。比如:組織的願景、管理者的使命。
杜拉克小說的價值在於:它們讓讀者意識到,真正至關重要的管理學議題,恰恰是無法用管理學教材去談論的。所有管理學教材都在強調:管理者必須承擔責任,管理者必須確定使命,管理者必須為組織規劃願景。這樣說固然沒錯,但這樣說並無太多實際意義。因為,沒有人會因為責任「有用」而承擔責任,沒有人因為組織「需要」願景就能憑空為組織杜撰出願景。真正擔負責任的人,只能在生活的洪流中發現責任。真正洞悉使命的人,只能在生活的挑戰中理解使命。沒人能在支離破碎的生活中領會使命,沒人能從支離破碎的生活中發現責任。凡是想要對組織負責的管理者,先得對自己的生活負責。對生活負責前提是,他得努力獲得關於生活的整全視野。
《最後的美好世界》裡,銀行家辛頓終生感念數學恩師黎曼。因為他從黎曼那裡學到了發現責任、確定責任的方法:「不要定義單一問題,應將問題組織成集合。」接下來的問題是:什麼才是正確的集合。一開始,人們往往會把看似奇特、無法歸類的事情排除到集合之外。可是或許會有某個時刻,他猛然發現,看似不相干的東西其實屬於同一集合。那樣的時刻,他會覺得茅塞頓開、耳清目明,因為他有可能正在接近集合的真正特殊之處。重新定義集合、定義正確的集合,不是往舊集合裡裝進新東西,而是由於有了新的視野和洞察,用全然不同的方式組織經驗、理解經驗。世界沒有變,觀看世界的眼光卻從此改變。原先無足輕重之事,在新的視野裡可能性命攸關。這種視野轉換,杜拉克在小說裡稱之為黎曼箴言。在另外的地方,他稱之為「新世界觀」(《 明日的地標》Landmarks of Tomorrow,1957)。自從獲知這個黎曼箴言,辛頓一直堅持藉助它理解生活、認識自我,尤其是在人生的重大時刻。小說裡,他正面臨這樣的時刻。他發現,自己必須把事業、婚姻、家庭、情慾串聯成完整的故事,才能理解當下的處境,才能基於真正的理解做出抉擇。不只辛頓,小說裡的每個人物,都在試圖理解屬於自己的那個完整故事,努力面對那個完整故事。這樣的故事,不屬於惡棍也不屬於聖徒,而是屬於被命運洪流、歷史洪流裡挾著,依然願意承擔責任的人。找到這樣的故事,也就找到了黎曼所謂的正確定義的集合,或者說,關於生活的整全視野。
《行善的誘惑》同樣描寫整全視野的獲得。藉助一場辦公室風波,杜拉克把生活的視野擴展到令人驚異的幽深之處:人們除了要面對慾望、事業、責任、使命,還得面對神性、魔性。對於杜拉克而言,神性、魔性,是理解現代生活的至關重要的維度。事實上,他的全部作品,都隱含著真誠的神學興味。從第一本書到最後一本書,他都在認真的談論惡魔,提醒世人,惡魔隨時可能重臨人間。借用黎曼箴言的表達法:如果把神性、魔性排除在外,管理者恐怕無法定義正確的集合。
杜拉克一生的寫作,始於剖析「經濟人」社會的窮途末路。而杜拉克留給後集權世界的最偉大的貢獻,是感召和塑造「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卓有成效的管理者」,恰恰是卓有成效的「經濟人」的反面。「經濟人」是喪失了對生活的理解力的人。杜拉克期盼的「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必須在管理這樁偉業中理解自己的生活。管理他人之前,他們得首先致力於在生活裡發現自己。在小說裡,「發現自己」不是乾癟的概念,而是活生生的生活。小說家杜拉克希望向讀者呈現的是,在概念和公式、操作指南之外的真正重要的東西:「男人和女人,以及人的行為、痛苦、喜樂、思想和情感。」(辛頓語)
五、最後的美好世界
識別極權、抵禦極權,是杜拉克終生貫之的思考基點。依照杜拉克的分析,一個社會之所以接納極權、擁抱極權,乃是源於群眾的絕望。而群眾的絕望還有一個更深的心理根源,那就是對某種完美世界的崇拜和期望。「經濟人」的世代,人們寄望於通過某種經濟模式、制度公式抵達完美世界。希望破滅,於是人們轉而委身非理性的瘋狂。對完美世界的群體迷戀,不止發生於19 世紀,也不會終結於20 世紀。事實上,這種迷戀,是深植於人類本性中的痼疾。
期盼某個完美世界,這本身不成問題。問題在於,人們把期盼錯放了位置。「完美世界」,本該是靈魂救贖的比喻。靈魂的救贖,只能發生在時間之外的永恆國度。可是,人們錯把對永恆國度的渴望錯置於塵世生活。人們不耐煩指向永恆的信心、盼望、愛慾,轉而熱衷於在塵世生活建構一勞永逸的完美。這種心態,杜拉克稱之為「社會救贖」的執念。這是一切極權的心靈土壤。極權政治的特徵之一,恰恰是以建造天堂為出發點,把人間變成地獄。杜拉克的終生努力,是喚醒世人對「社會救贖」的執念。《旁觀者》裡,杜拉克曾藉著談論他與卡爾.波拉尼的異同,區分「完美社會」和「尚可忍受的社會」:
在「完美的社會」這種觀念仍主宰一切的今天,要追尋這種社會,可能會使我們的世界陷於無法容忍,完全失去自由,或是引發自我毀滅的戰爭。
我則願意以一個充裕、能讓人忍受且自由的社會取而代之,也就是我在《工業人的未來》一書中提到的。這麼一個社會也許是我們所能希冀的最好的一個。我們可以藉著付出一點代價,亦即藉由市場的分裂、分隔和疏離來維繫自由。為了個人,衝突、冒險以及走向多元化等代價也是我們可以付出的。
捍衛「尚可忍受」的世界的人們,深知人性的不可靠。他們同樣深知,及身之責任、及身之努力,是唯一可靠之事。人們知道自己身為有限的受造物,不可能在有限的時空世界裡達成完美;但人們也知道,身為上帝的造物,自己有責任在一個不夠完美的社會裡各盡責任,彼此照料、創造、修補、傳承、守護。一個「尚可忍受的社會」,就是一個運轉良好的「功能社會」(A Functioning Society)。杜拉克探究工業社會、公司治理、聯邦分權、非盈利組織,都是意在描述一個功能社會所必需的元素。
伏爾泰在《憨第德》裡說了一句或許源自萊布尼茲的格言:「這個世界是『可能出現的世界中最好的一個』。」杜拉克把「最好的」,改成「最後的」。他提醒人們:每個有死之人,都該珍視他所身處的「這一個」世界;如果他願意盡力讓世界變得「更好」而不是「最好」,如果他不再相信砸碎地獄收穫天堂的謊言,那麼他所身處的「這一個」世界,是他唯一的機會。《最後的美好世界》裡,索別斯基親王說出了這個意思:
這是最後的美好世界了,群體和階級彼此共存,不會相互廝殺,或一頭栽進內戰。一旦改變這個世界,某個群體就會起而統治,無論是富人收買軍隊射殺窮人,還是窮人把嫉恨發洩在其他人身上,其實都不是關鍵。關鍵在於,到時候所有讓人值得活下去的東西,所有的平衡與多元、包容與選擇,也就是我們稱為文明的一切,都將蕩然無存。
意識到自己對「最後的美好世界」負有責任,這是人之為人的重要發現。人發現自己既非天使,也非魔鬼。不是天使,所以人得克服自我封神的誘惑;不是魔鬼,所以人得拼盡全力抵擋魔鬼。什麼樣的人能夠抵禦魔鬼呢?唯有那些能夠在命運和生活的洪流裡發現責任、理解責任、承擔責任的人。他們並不否認自己的慾望,同樣也不逃避自己的責任;他們在自己身上看見魔性,同樣也尊重自己身上的神性;同時帶著神性和魔性,他們願意把握唯一的機會,過出有人性的生活。
《最後的美好世界》第四部,一位見證了19 世紀歐洲興衰的老祖母追憶平生。她感歎:19 世紀之所以值得懷念,是因為這個世代不只有城市膨脹、技術爆炸、資本繁榮。除了這些,19世紀到底還擁有一些能夠理解信仰、責任、和美的人物。老祖母把她見識過的人物分成三類:
藝術家,是那種渴望創造的人。一位造橋藝術家,不會問「你喜歡這座橋嗎?」,而是問:「山谷裡有了這座橋,看上去如何?」這位藝術家或許並不信仰上帝。但他卻會在自己的作品上題寫「愈顯主榮」。寫下這句話時,他想到的不是什麼神學教條,他只是渴望為這個美好的世界增添新的美好。
匠人,是那種願意在任何可能的事情上施展才智的人。他們的才智可能用於打磨器物、製造槍炮,也可能用於管理企業、謀劃生意。他們的才智就在於,講究紀律,講究方法,無論投身哪個領域,他們都能高效地把事情辦成,辦好。
老祖母說,任何世代都不會缺少這兩種人。尤其是匠人,未來的世代或許會越來越多。沒有匠人式的人物,文明根本無法存續。問題在於,如果只剩下匠人,那樣的文明或許根本算不上文明。老祖母真正擔心的,是第三種人的消亡,那就是她所謂的「貴族」。她的例證,是小說裡未曾正式出場的哥哥。這位哥哥,曾經是革命青年,相信只要砸碎舊世界,就可以造就人間天堂。後來,他從革命癔癥中醒來,成為建築商人。但他從來不是一個「純粹」的商人。因為他的興趣從來不只是蓋房子和營利:
年輕時我信奉憲法,隨時準備為憲制政府、為成人選舉權、為議會選舉、為新聞自由而犧牲生命。我的目標是建立一個自由、公正的社會,這個目標終生不變;1848 年我們年輕人站上路障,就是夢想建立這樣的社會。但很久以前我就認識到,這個目標無法透過憲法達成。實現這個目標的方法在於栽培公民,而不是制定憲法。公民是在家裡養成的。在一個人的成長過程中,若是周遭的環境能把尊嚴、自尊和責任感注入他的靈魂,他就會長成一個公民。我依舊是個革命者。過去四十年來,我建造的每一棟建築都是我的革命宣言。我依舊對高尚的羅馬共和國體制懷有夢想; 在反動勢力肆虐的令人沮喪的1830 年代,身為小學生的我們便已經對它宣誓效忠。但現在我已明白,布魯特斯的匕首只會造就另一個暴政。建設者的工具,而非殺人者的工具,才是正確的工具。我的目標就是要建設一個讓公民能夠抬頭挺胸地生活的人性化的環境。
老祖母說,這位哥哥是她心目中真正的「貴族」。真正「貴族」的標誌,不是對族譜念念不忘,而是對責任念念不忘。這位貴族,年輕時為了某個「完美世界」而革命。後來,他把認真蓋房當成自己的革命宣言。蓋出讓人挺胸生活的房子,這是他對「最後的美好世界」所盡的責任。
小說的第四部,題為「致音樂」。杜拉克也建議讀者,把他的故事讀成一部「協奏交響曲」。所謂「交響曲」之美,正在於每種樂器、每個聲部各自伸張個性,又能在更宏大的層面上衝突、競爭、和解、合作,臻至和諧。20 世紀的種種革命,都以審判舊世界、砸爛舊世界為號召。杜拉克卻想提醒讀者,那個早已逝去的舊世界,自有其音樂之美。它的美好之處在於:有各種各樣的人物,有各種各樣的事業,有各種各樣的責任和生活。匠人、藝術家、貴族、國王、公民可以在那樣的世界裡各司其職、各盡其責。他們之間並非只有鬥爭、殺戮,他們已經在學著相互照料、彼此促進。每個人的生活裡,也不只有掙扎、鑽營;除了用力生存,人們還有能力發現責任、欣賞藝術、享受愛情。這樣的世界,有苦難、有罪惡,也有為了自由、尊嚴、美好而盡心盡力的人們。它絕不完美,但它至少為願意承擔責任的人們提供著機會和舞台。這就是杜拉克心目中的「尚可容忍」的社會,或曰「最後的美好世界」。那些親手把它毀掉的人遲早會意識到,他們毀掉了自己最後一次建設美好世界的機會。
老祖母帶著憂慮展望將要到來的20 世紀。她不知道,20 世紀是否還能為自己培養「貴族」,或是帶有「貴族」氣質的藝術家和匠人。如若不能,那將會是怎樣的世紀?一場音樂終了,取而代之的未必是另一場音樂。世界很可能貧瘠到只剩下喧嘩、騷動、革命口號、機器轟鳴。
彼得.杜拉克在20 世紀末寫了兩本小說。他用兩本小說問出了跟老祖母同樣的問題。他的兩本小說,不只是留給世人的問題,也是留給世人的建議。這份建議,不像管理學教材那樣,為管理者們提供明確的操作指南。杜拉克用小說向所有管理者展示了他們必須面對的生活。這些渴望「卓有成效」的人,首先必須對自己的生活保持真誠。唯有如此,他們才能在生活裡發現人之為人的真實境況:責任、使命、神性、魔性、兼染神性與魔性的人性,以及,他們必須珍視的「最後的美好世界」。杜拉克不止一次強調:管理學是關於人的學問。這些事情,正是至關重要的人的學問:不是指向他人的學問,而是指向自己的學問。